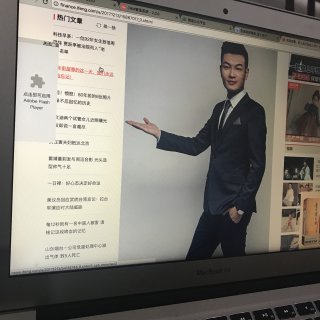作者:XIN
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9胡潤財富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底,大中華區擁有600萬資產的“富裕家庭”(“家庭”戶平均規模為三人)數量已經達到494萬戶,其中擁有600萬可投資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達到178萬戶;這些“富裕家庭”所擁有的總財富已經達到128萬億,是大中華區全年GDP的1.3倍,其中,中國內地占八成。這128萬億中,擁有億元人民幣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總財富為77萬億,占比60%;擁有3000萬美金資產的“國際超高凈值家庭”總財富為72萬億,占比56%。在128萬億的總財富中,預計有17萬億將在10年內傳承給下一代,39萬億將在20年內傳承給下一代,60萬億將在30年內傳承給下一代。[1]

體量龐大的財富如何避免意外事件的干擾而實現有序傳承,已成為財富創造者們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其中所涉及的稅務問題更是重中之重。不同安排下的稅務負擔直接決定了可傳承財富的實際價值,而確保稅務合規也是具體方案得到有效執行的先決條件,從而真正實現財富而非“稅務隱患”或“債務”的承繼。高凈值人士財富傳承,財富保值甚至增值的客觀需求,催生了市場上的各類信托安排,金融工具,壽險保單,理財產品等等。不同的方案和工具可能涉及各類不同的稅務影響,甚至在跨境安排中還會涉及不同司法管轄區域內差異的稅收系統和制度。
本文篩選我們在實踐中遇到的某些典型場景,以虛擬案例的形式,向讀者概括介紹財富傳承在中國需關注的稅務事宜,希望對有需要的人士有所幫助,對從事相關業務的同儕有所裨益。受篇幅所限,本文僅能如蜻蜓點水,對財富傳承規劃中的部分稅務考量稍作分析,未來希望得空以系列文章形式進一步探討各類花式家族財富架構中的稅務那些事兒。
原中國公民丁先生,80年代赴美留學攻讀醫學物理博士,畢業后留美工作并加入了美國籍。丁先生在美留學期間邂逅美籍華人丁太太,二人婚后育有一子(“丁子”),后者持有美國護照。
丁先生學業有成后,打算回國發展。因丁太太不愿回國且雙方感情破裂,二人離婚。隨后丁先生獨自一人帶著兒子回國發展,與其他合作伙伴、投資人共同創辦了國內C公司,主要從事原研藥的研發與制造。
丁先生在創辦國內C公司時聽取了專業顧問的建議,采用了間接持股的架構,系通過一家香港控股公司持有國內C公司的股權。香港控股公司的直接股東包括:丁先生個人設立的100%持有的開曼公司(持有香港控股公司60%的股權),另一家投資機構以及其他公司核心骨干(共同持有香港控股公司剩余40%的股權)。
此外,丁先生對其個人資產進行了一定規劃及配置,其中主要包括國內的一些房產(均登記在丁先生個人名下)、壽險保單、古董字畫等。
丁先生生前未訂立遺囑,但于2017年經專業人士建議,設立了一份離岸信托,并將香港控股公司60%的股權(通過自己100%控制的開曼公司),以及其他現金資產轉移到離岸信托下。信托的受益人系丁先生的兒子,該信托安排約定丁先生去世后,受托人(某離岸信托公司)將香港控股公司60%的股權分配給受益人,對于其他現金資產由受托人進行投資,每年按照規定的數額向受益人分配投資收益。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導致丁先生不幸去世。丁先生去世時父母依然健在,其均為中國人并長期生活在國內。

對于涉及跨國財富傳承的安排,從稅務角度首要需厘清的是相關利益主體個人的稅收居民身份以及相關所得的來源地認定規則。
丁先生及其子作為美國公民,構成美國稅收居民。但同時,鑒于丁先生及其子常年居住在中國境內,根據中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有關規定,丁先生及其子同時構成中國稅收居民。[2]
作為中國稅收居民,丁先生及其子可能需就其無論來源于中國境內還是境外的所得,在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具體取決于他們構成中國稅收居民個人的類型(例如,系屬于在中國境內有住所的居民個人vs.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但在中國境內居住達183天的居民個人)。同時,丁先生及其子作為美國稅收居民,需就其所得在美國繳納個人所得稅,從而導致就同一筆收入雙重征稅的問題。
為盡可能避免雙重征稅的問題,結合各實際案例具體情況,通常有不同的稅務規劃方案可供考慮。例如,最為簡單的方式是對個人在國內的居住時間進行控制,但該方式主要適用于無住所個人。對于某些重大復雜的情形,可考慮中美雙邊協商程序等。
根據中美稅收協定有關規定,當某自然人同時被中、美兩國的國內稅法認定為稅收居民個人,中美雙方的稅務主管當局應當協商確定該人為一方納稅居民。[3]根據《中美稅收協定》之議定書第五款[4],中美稅務主管當局在進行確定程序時應以如下標準為準:
(一)應認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國的居民;如果在兩個國家同時有永久性住所,應認為是與其個人和經濟關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國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國無法確定,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國都沒有永久性住所,應認為是其有習慣性居處所在國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兩個國家都有,或者都沒有習慣性居處,應認為是其國民所在國的居民;
(四)如果其同時是兩個國家的國民,或者不是其中任何一國的國民,應由締約國雙方主管當局通過協商解決。

近些年來離岸信托架構日趨普遍,國內不少家庭已搭建離岸信托。但很多人雖說搭建了離岸信托,卻對離岸信托的真正功能缺乏實際了解,僅是通俗的以為可以“避稅”,殊不知其中可能隱藏稅務及其他法律隱患,而且有可能無法充分實現風險隔離、有效傳承、節約稅負的效果,得不償失。事實上,離岸信托的搭建是一項技術性相當強的工作,其中涉及多法域眾多法律及稅務事項,需要綜合考慮、統籌安排。下文我們從中國稅務角度對離岸信托中涉及的部分稅務問題進行分析:
a) 信托設立和注入信托財產時的稅務問題
丁先生作為委托人,通過自己100%持有的開曼公司將香港控股公司60%的股權注入離岸信托。在交易形式上是一個純粹的離岸交易,即,境外非居民企業(開曼公司)向離岸信托公司下設的某境外公司轉移香港控股公司股權的行為,但因為香港控股公司持有中國境內C公司100%的股權,根據中國稅法的有關規定,該交易有可能被中國稅務機關認定為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
具體而言,根據《關于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7號,以下簡稱“7號公告”)的規定,“非居民企業通過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規避企業所得稅納稅義務的,應按照《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5]的規定,重新定性該間接轉讓交易,確認為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
7號公告第三條規定,“判斷合理商業目的,應整體考慮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相關的所有安排,結合實際情況綜合分析以下相關因素:
(一)境外企業股權主要價值是否直接或間接來自于中國應稅財產;
(二)境外企業資產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構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主要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中國境內;
(三)境外企業及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稅財產的下屬企業實際履行的功能和承擔的風險是否能夠證實企業架構具有經濟實質;
(四)境外企業股東、業務模式及相關組織架構的存續時間;
(五)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在境外應繳納所得稅情況;
(六)股權轉讓方間接投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與直接投資、直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的可替代性;
(七)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所得在中國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情況;
(八)其他相關因素。”

根據上述7號公告的規定,信托安排存在著被稅務機關認定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進而重新定性為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的風險,盡管如此,理論上仍有空間避免繳納所得稅。一方面,如果有充分事實基礎和證據說明該類離岸信托安排并非出于規避稅負目的而設立,而是有現實的保障家族財富安全的需求,以及出于未來利于財產繼承的目的而創設,這種情形下有機會證明是具備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另一方面,在信托安排下丁先生下設開曼公司通常是按照零對價或名義對價向信托轉讓香港控股公司股權,換言之,該交易下開曼公司并未直接產生股權轉讓所得,除非未來該交易的轉讓價格被稅務機關進行納稅調整。
此外,除了選擇通過名下開曼公司轉讓香港控股公司60%的股權外,丁先生還可以選擇個人直接將名下開曼公司100%的股權轉移到離岸信托下。由于7號公告僅適用于非居民企業而不適用于個人,丁先生對于開曼公司的股權轉讓不會直接受7號公告管轄。不過在2019年新施行的個人所得稅法下,其首次正式引入了針對個人所得稅的反避稅條款。[6]從一般反避稅的角度來看,如果離岸控股公司缺乏足夠的商業實質,中國稅務機關有可能穿透該公司,將丁先生對開曼公司的股權轉讓視為直接轉讓中國C公司的股份。對于沒有合理經營目的的無償轉讓或者低于市場價格的轉讓,稅務機關可以依據獨立交易原則,以轉讓時股權的市場公允價值為標準,核定股權轉讓所得并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是,對于信托安排是否會被認定為缺乏合理商業目的,目前稅法并未有明確規定,理論上如前所述,對于一些信托交易安排,應有機會認定其具備合理商業目的。
丁先生在信托設立階段,按照信托合同的約定,將現金財產注入離岸信托,使受托人成為信托財產的名義所有權人。針對該行為,我國現行的稅收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規定個人現金轉讓或現金贈與的稅務處理。此外,中國并未開征贈與稅。實踐中,對于信托安排下的現金資產轉讓,通常未見征收所得稅的案例。
b) 丁先生去世后,丁子從信托下取得收益分配時的稅務問題
關于受益人從信托中取得的收益分配,主要涉及受益人的個人所得稅影響以及轉讓方(即,信托公司下設的持股平臺)處置信托財產的稅務影響。我國當前的稅收法律法規尚未對此予以明確,各地稅務機關在實踐中可能對該種所得的性質存在不同理解,對受益人是否應當繳納個人所得稅,以及按照何種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可能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另外,對于信托公司向丁子直接分配香港公司股權的行為,從轉讓方角度而言,該交易有可能被視為屬于7號公告項下間接轉讓中國公司股權的交易。
c) CRS的相關影響
信托賬戶的涉稅信息是否會依據CRS進行交換,取決于相關參與者的稅收居民國(地區)是否參與了CRS并與中國建立了交換關系。針對境外信托,如果委托人、受益人、監察人/保護人是中國稅收居民,且信托本身的稅收居民身份國(地區)為與中國建立交換關系的CRS參與國(地區),則中國稅收居民的信托賬戶涉稅信息可能會被報送給境外稅務機關,再由境外稅務機關將該信息自動交換給中國稅務機關。[7]
具體而言,在CRS下,信托計劃本身作為一個實體,既可能構成金融機構,也可能構成非金融機構。CRS下的金融機構主要包括存款機構、托管機構、投資機構以及特定保險機構。信托計劃本身有可能符合“投資機構”的認定條件而被視為一家金融機構。如果信托計劃本身構成金融機構,一般需要由擔任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將信托賬戶持有人的信息申報至稅務機關,并由稅務機關進行自動交換。相反,如果信托計劃不構成金融機構,則為非金融機構。只有當信托在其他金融機構開戶時,才涉及到被其他金融機構進行CRS識別和申報的問題。在此情形下,信托計劃在參與CRS的司法管轄區(如中國)的金融機構開立賬戶時,會被:
信托的稅收居民身份,通常由受托人的稅收居民身份決定。如果信托計劃為與中國建立CRS交換關系的司法管轄區的稅收居民,則信托計劃賬戶信息會被申報;并且
根據信托計劃的收入、資產的性質,判定是否需要穿透信托,對信托的實際控制人進行申報。
按照信托收入、資產的性質的不同,信托作為非金融機構,又可分為“積極非金融機構”和“消極非金融機構”[8]。構成積極非金融機構的信托僅需披露和交換信托本身信息,而構成消極非金融機構則會被穿透至實際控制人[9],根據實際控制人的居民身份決定是否進行申報。
在上述案例中,丁先生去世時名下在中國有房產,因生前未訂立遺囑,因此應按照相關法律確認繼承人,本文因著重分析稅務問題,不展開論述關于丁先生遺產繼承應適用的法律問題。茲假設丁先生的中國境內房產,由其父母和兒子繼承,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中國房產繼承相關的稅務影響。
a) 增值稅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過渡政策的規定》(財稅[2016]36號附件3)第三十六條規定,涉及家庭財產分割的個人無償轉讓不動產、土地使用權,免征增值稅。家庭財產分割,包括下列情形:離婚財產分割;無償贈與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兄弟姐妹;無償贈與對其承擔直接撫養或者贍養義務的撫養人或者贍養人;房屋產權所有人死亡,法定繼承人、遺囑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依法取得房屋產權。
依據上述規定和《繼承法》,丁的兒子、父母作為丁的法定繼承人繼承其中國房產可以免征增值稅。
b) 個人所得稅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無償受贈房屋有關個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78號)第一條規定,以下情形的房屋產權無償贈與,對當事雙方不征收個人所得稅:
(一)房屋產權所有人將房屋產權無償贈與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兄弟姐妹;
(二)房屋產權所有人將房屋產權無償贈與對其承擔直接撫養或者贍養義務的撫養人或者贍養人;
(三)房屋產權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產權的法定繼承人、遺囑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
根據上述規定,丁的兒子、父母作為丁的法定繼承人繼承其中國房產可以免征個人所得稅。需要注意的是,當繼承人未來轉讓該房產時,須計征個人所得稅,其應納稅所得額為轉讓收入減去被繼承人購置房屋支付的價款、轉讓過程中繼承人支付的相關稅費后的余額。因此,繼承所產生的僅是納稅遞延的效果,并未免除房產增值所帶來的個稅負擔。
c) 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規定,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著物并取得收入的單位和個人,為土地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應當依照條例規定繳納土地增值稅。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著物并取得收入,是指以出售或者其他方式有償轉讓房地產的行為。不包括以繼承、贈與方式無償轉讓房地產的行為。
依據上述規定,丁的兒子、父母繼承其中國房產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稅。
d) 契稅
現行有效的《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繼承土地、房屋權屬有關契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4]1036號)規定,對于《繼承法》規定的法定繼承人繼承土地、房屋權屬,不征契稅。
根據上述規定和《繼承法》,丁的兒子、父母作為丁的法定繼承人繼承其中國房產可以免征契稅。
e) 印花稅
現行國家層面印花稅相關政策并未對繼承下的房產過戶是否繳納印花稅作出明確規定,因此在實操層面需了解房產所在地的具體印花稅政策及實踐。據我們的經驗,大部分地方對房產繼承應不會按照財產轉讓征收印花稅。

對于丁先生生前購買的壽險保單、古董字畫,從中國稅法角度,并未對通過遺產繼承方式取得上述財產做出專門的規定,同時中國并未開征遺產稅,因此實踐中上述遺產繼承在中國不會產生稅負。
本文的案例雖是虛構的,卻是從我們日常經辦的家族財富傳承業務中提煉的精簡版。現實中的情況遠比上述案例更加紛繁復雜,會涉及更多方面的稅務規劃和稅務影響。譬如上文僅就一些典型的中國國內稅法涉及的稅務問題作了簡單闡述,未涉及美國稅務問題,也未涉及在遺產繼承過程中常見的財產糾紛、公司控制權交接等實際棘手問題。實踐中出于積極防御、應對上述現實問題的考慮,往往需要對整體財產傳承方案作出調整,其中涉及的稅務問題會變得更為復雜,而合規有效的稅務規劃也就顯得尤為重要。